 |
城市和城墙 |
|
西安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让人叹为观止的兵马俑,不是令人浮想联翩的华清池,而是它的古城墙。
西安的城墙管理很人性化,每隔一段就有出入口,而且收费低廉。一个深秋的日暮时分,我从一处瓮城上去,极目四望,但见人烟辐辏,一望无际。在上面差不多绕了一圈,直到暮色渐行渐沉,行人渐行渐散,才兴尽归去。回想汉唐盛时,站在城墙上所能够看到的恐怕是五里一短亭、十里一长亭的驿道,还有,折柳相赠,执手相看泪眼的远行人吧?!
城墙是古时城池的防御系统,是自卫的手段,亦是封闭自守的渊薮。当然,有闭必有启,有城墙就有城门,也有了城门的启闭时间和制度。而这,又往往在客观上影响了住在城内外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仿佛现在从市区开往郊区的公交车,其末班车的时间往往决定了住在郊区的人们是否能够看完夜场电影或者是否有兴趣在晚饭后到市区去逛逛。同时,这也影响了夜市的热闹程度和商人们利润的高低。
建国初年,几乎所有城市的城墙都被当作阻碍新中国建设的封建糟粕,一纸命令下来,霎时均化为乌有。梁思成和林徽因为北京古城墙呐喊请命的呼声也被理所当然地湮没在热火朝天的时代洪流里,微弱得可以忽略不计。据说,这两位古建筑专家心情复杂地捡了墙砖回家,视若拱璧。
不过,有形的城墙虽然拆除了,但其影子却顽强地坚持留在我们的生活里,不肯撤离。比如北京,同一条大街却往往被分成内、外两段,就像阜成门内大街和阜成门外大街。走在这些街上,你会觉得仿佛城墙还在那里,无言地诉说它曾经的存在。
我所居住的杭州也一样,城墙是早就连断垣残壁都看不到了,但城门的名称却几乎完全保留了下来,只不过,它们不再是城区和郊区的分界线,而是城市某一个区域的代称。比如武林门,现在是最著名的闹市区;又如艮山门,现在是交通枢纽。而清波门、涌金门、凤山门等,也都代表着某一片城区。柳永赞颂杭州的繁华,曾说“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他若是看到如今六七百万人口、日新月异的杭州城,怕是会惊讶得提不起笔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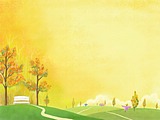
|
|
|
